男女主角分别是周明轩明轩的其他类型小说《结局+番外窒息!那个只说我妈不容易的男人周明轩明轩》,由网络作家“化道3000”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切菜、调味。我尝试做他心心念念的红烧肉,结果错把糖当成了盐,一锅肉烧得黢黑发亮,味道更是惨不忍睹。我沮丧得快要哭出来,他却笑着夹起一块,煞有介事地品尝,然后夸张地说:“嗯,独家秘制,咸味红烧肉,别有一番风味!下次记得申请专利。”他眼里的笑意,比窗外落日熔金的晚霞还要温暖,将我所有的懊恼和不安都轻轻拂去。那时,我觉得,所谓的幸福,大概就是这样,两个人,一间小屋,三餐四季,即使偶尔有小小的失误,也能被爱和包容温柔化解。我们搬进这个宽敞明亮的新家时,我以为幸福会随之升级,空间大了,心也该更敞亮才是。明轩工作日益繁忙,应酬也多了起来,常常带着一身酒气和疲惫回家。我理解他为这个家的付出,于是努力扮演好一个“贤内助”的角色,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结局+番外窒息!那个只说我妈不容易的男人周明轩明轩》精彩片段
切菜、调味。
我尝试做他心心念念的红烧肉,结果错把糖当成了盐,一锅肉烧得黢黑发亮,味道更是惨不忍睹。
我沮丧得快要哭出来,他却笑着夹起一块,煞有介事地品尝,然后夸张地说:“嗯,独家秘制,咸味红烧肉,别有一番风味!
下次记得申请专利。”
他眼里的笑意,比窗外落日熔金的晚霞还要温暖,将我所有的懊恼和不安都轻轻拂去。
那时,我觉得,所谓的幸福,大概就是这样,两个人,一间小屋,三餐四季,即使偶尔有小小的失误,也能被爱和包容温柔化解。
我们搬进这个宽敞明亮的新家时,我以为幸福会随之升级,空间大了,心也该更敞亮才是。
明轩工作日益繁忙,应酬也多了起来,常常带着一身酒气和疲惫回家。
我理解他为这个家的付出,于是努力扮演好一个“贤内助”的角色,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精心准备他喜欢的饭菜,等他晚归。
只是渐渐地,餐桌上的对话越来越少,他更多的时候是沉默地吃饭,或是对着手机处理工作。
我精心烹饪的菜肴,似乎也失去了被欣赏的意义,只沦为果腹的必需品。
而婆婆的“关心”,则像初冬的第一场薄雪,悄无声息地,开始覆盖我们生活的角角落落。
最初,只是偶尔的电话叮嘱。
“微微啊,明轩最近加班多,你要多给他炖点汤补补。”
“你们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要懂得节省,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这些话,我尚能当作长辈的善意提醒,左耳进右耳出,尽量不往心里去。
直到上周末,我外出参加一个翻译沙龙,回到家时,发现家里“焕然一新”。
客厅的抱枕换了方位,阳台上的绿植被修剪得有些呆板,而最让我感到不适的,是书房——我视若私人领地的地方。
我那些按照类别和阅读习惯摆放的书籍,被她按照高矮顺序重新排列,书桌上我随手放置的笔记本和笔,被整齐地收进了抽屉,甚至我床头柜上放着的一本诗集,也被塞到了枕头底下,取而代之的是一本封面花哨的《育儿百科》。
我站在书房中央,像一个闯入陌生空间的旅人,心里说不清是愤怒还是委屈,更多的是一种边界被侵犯后的窒息感。
那不是简单的整理,那是一
”,所谓的“家庭开支”,背后隐藏着这样不为人知持续不断的输血。
我不是反对他孝顺父母,给他母亲钱是应该的。
让我感到彻骨冰冷的,是他的隐瞒,是他这种区别对待的方式。
他可以为了满足母亲的需求,背着我动用我们共同的积蓄,却在我提出合理需求时以“手头紧”来搪塞。
这种不透明,这种不平等,像一把钝刀子,缓慢地割裂着我们之间仅存的那点信任和夫妻情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苏雅说的“装睡的人”。
他不是不知道问题所在,他只是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最省事的方式——对我隐瞒,对母亲顺从。
他用这种方式,维持着他和他原生家庭那个牢不可破的联盟,而我,这个所谓的“妻子”,不过是被蒙在鼓里的局外人,一个在他精心构建的“家”的剧本里,扮演着配合角色的工具人。
心底那片积蓄已久的湖水,终于冲破了堤岸。
不是愤怒的爆发,而是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平静。
所有的犹豫、不舍、对过往温情的最后一丝留恋,都在这几张冰冷的转账凭证面前,灰飞烟灭。
我没有立刻打电话质问他,也没有歇斯底里地摔东西。
我只是小心翼翼地将文件夹放回原处,关上抽屉,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然后,我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像是在看自己灰暗一片的未来。
不,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废墟之上,破土而出,带着一种决绝的生命力。
我不能再待在这个充满了谎言和不尊重的“家”里,不能再扮演那个被蒙蔽、被牺牲的角色了。
那天晚上,明轩加班回来,带着一身疲惫。
他像往常一样,换鞋,洗手,然后坐在沙发上,问我晚饭吃了什么。
我看着他,他的脸在灯光下显得有些憔悴,眉宇间有掩饰不住的倦意。
若在从前,我或许会心疼,会递上一杯温水,会关心他工作是否顺利。
但此刻,我只觉得眼前的这个人,无比陌生,无比遥远。
“明轩,”我开口,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有些惊讶,“我们谈谈吧。”
他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会主动挑起话题,而且是用这样一种异常冷静的语气。
“谈什么?”
“谈我们。”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不闪
敛了许多,只是偶尔还会旁敲侧击几句。
我通常以沉默或简短的“嗯”、“知道了”回应,不再试图解释或辩驳。
她那些曾经能轻易点燃我怒火或委屈的话语,如今像投进深潭的石子,连一丝涟漪都难以激起。
我的世界,开始向内收缩,也向外延展——只是延展的方向,不再包含明轩和这个“家”。
我重新联系了那位编辑,虽然婉拒了那个需要出国的翻译项目,但我请求她未来若有合适的远程项目,可以优先考虑我。
然后,我将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手头的工作中。
每一个精准的用词,每一段流畅的译文,都像是在混乱的生活中重新搭建起的一小块秩序。
在文字的世界里,逻辑清晰,因果分明,付出便有回报,这种掌控感,是我在现实婚姻中早已失去的奢侈品。
除了工作,我还重新拾起了画笔。
大学时我曾短暂地迷恋过水彩,后来因为恋爱、结婚、融入家庭而被束之高阁。
如今,在那些颜料与水交融的氤氲变幻中,我仿佛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角落。
我画窗外的流云,画桌角的孤灯,画那些无法言说的情绪,任由它们在画纸上流淌沉淀。
专注的时刻,外界的喧嚣和内心的冰冷似乎都暂时退去,只剩下笔尖与纸面摩擦的沙沙声,和一种久违的纯粹宁静。
我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静,像一个局外人一样,观察明轩,观察这个家。
我回想起过去的种种细节:他每次在我与婆婆发生矛盾时的和稀泥;他在朋友面前对我那些“小情绪”的不耐烦;他在经济上对我自由职业隐隐的不认同……那些曾经被我用“他太累了”、“他只是不擅表达”、“他本意是好的”等理由强行合理化的行为,如今在清醒的目光下,拼凑出一个更令人心寒的真相——他的世界里,他母亲的感受、他的面子、所谓的“家庭和睦”永远排在我的需求和感受之前。
他并非不爱,只是他的爱,有太多的前提和保留,有太重的原生家庭的烙印,沉重到足以将我微薄的期待碾压成粉末。
我也反思自己。
是不是我最初的过于隐忍,助长了他的理所当然?
是不是我一次次的退让,让他习惯了我的牺牲?
是不是我从未真正清晰、
窒息!
那个只会说“我妈不容易”的男人,亲手毁了我们的家。
当婚姻只剩算计和谎言,我选择自救!
01午后的阳光,像融化的金子,慷慨地洒满了整个客厅。
空气中浮动着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跳跃、旋转,如同一些无声的细碎秘密。
客厅的米白色沙发上,周明轩微微侧着身,听着身旁的母亲低声说着什么。
他脸上挂着我再熟悉不过的表情——一种混合了些微无奈,却又带着全然顺从的微笑,嘴角习惯性地向上牵引着,仿佛这样就能将那些或许并不那么悦耳的话语,都温柔地包裹起来。
茶几上,那套我精心挑选的汝窑茶具,正安静地吐纳着白色的氤氲。
那是明轩喜欢的龙井,清冽的香气试图弥漫开来,却似乎总被一种更沉闷的气息压制着,若有若无。
眼前的一切,从昂贵的橡木地板,到墙上我们结婚时放大的油画相框,再到沙发上母子间看似亲昵的低语,都严丝合缝地呈现出一种近乎完美的安稳,一种被世人普遍认可的“家”的温暖定义。
可我却不合时宜地,坐在书房靠窗的那把藤椅上。
阳光越过窗棂,同样炽热地落在摊开的书页上,烫得那些铅字仿佛都活了过来,想要挣扎着跳出纸面。
然而,这暖意却吝啬地停留在皮肤表面,丝毫无法渗透进我的指尖——那里,正残留着一丝令人心惊的微凉,仿佛刚刚触碰过深冬的寒冰。
书,其实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
我的目光,像一只疲惫的飞鸟,越过书页,穿过半开的书房门,落在客厅那幅“温馨”的画面上。
他们谈话的声音很轻,如同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模糊不清,但我能清晰地捕捉到明轩时不时点头的动作,和他母亲嘴角那抹不易察觉的满意弧度。
我像一个误入了别人戏剧舞台的观众,手足无措地坐在角落,看着台上的人们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上演着一出与我有关,却又似乎将我排斥在外的剧目。
明明身处同一个屋檐下,呼吸着同一片空气,我与他们之间,却仿佛隔着一条无声的河流。
河流之上,横亘着一道看不见却日渐增厚的冰层。
这道冰,它悄无声息地凝结,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响,只在每一次细微的呼吸间,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
种无声的宣告,宣告着她在这个家拥有随意处置的权力,而我的习惯和喜好,是可以被轻易忽略和覆盖的。
晚上,等明轩回来,我犹豫再三,还是委婉地提起了这件事。
“明轩,妈今天来过了……她帮着收拾了一下,挺好的。
就是……书房里的东西,下次能不能让她别动了?
我有些东西放习惯了,找起来方便。”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不带指责。
明轩当时正解着领带,闻言动作顿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那种我熟悉的试图息事宁人的表情。
“哦,妈也是好心,看你忙不过来,想帮你分担点。
她老人家就是爱操心,你别往心里去。”
“我知道她是好心,”我努力压下心头涌上的涩意,“但我希望……我的空间能保留一点自己的习惯。”
他叹了口气,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有些重,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
“微微,妈年纪大了,观念跟我们不一样。
她做这些,出发点总是好的,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你就多担待一点,啊?
为这点小事跟她计较,让她不高兴,多不好。”
“多担待一点……”这几个字像细小的冰锥,轻轻敲打着我的心房。
我看着他,他眼神里没有责备,却也没有理解,只有一种“这事就到此为止”的疲惫和不耐烦。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无比的无力。
我以为婚姻是两个人的同舟共济,遇到风浪时,他会是我最坚实的依靠,会站在我身前,为我遮挡哪怕一点点的风雨。
可现实却是,当来自他原生家庭的风雨袭来时,他首先选择的,是让我退到后面,“多担待一点”。
我的委屈,我的不适,我的那些细腻敏感的心思,在他看来,似乎都成了“小事”,成了“计较”,成了破坏家庭和睦的不懂事。
我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比如“那不是小事,那是我的边界”,比如“我不是计较,我只是需要尊重”,但最终,所有的话语都梗在喉咙里,化作了沉默。
因为我知道,再说下去,可能就会演变成争吵。
而争吵,除了带来更多的伤害和疲惫,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他不会明白,或者说,他不愿明白。
在他的世界里,“家和万事兴”似乎就是最高准则,而维系这份“和”的代价,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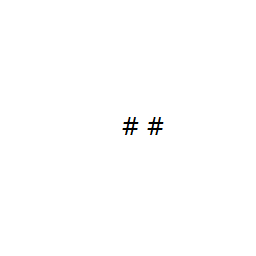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