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主角分别是沈砚海子的其他类型小说《碎光记忆 全集》,由网络作家“青青炒饭”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碎光》第一章:站在出发的车站1995年9月28日,沈砚十八岁。那天阳光很好,镇上的风像是被水洗过,干净、通透。他站在小镇火车站的候车厅里,脚边是一只蓝色的帆布袋,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一本发黄的诗集和一双未拆封的新袜子。候车厅的广播喇叭像几十年没修过似的,发出沙哑的金属声。候车室的木长椅被坐出了一层层油亮的光,角落里有个小孩在哭,母亲没说话,只是不停地拍着他的后背。沈砚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双手紧紧握着票根。去省城的火车下午两点四十到站。他在等,等这辆把他送出镇子的车,仿佛命运也被塞进了那节车厢。“到了那边,先去找你二叔。他在建筑公司,能帮你安排个工地干活。”父亲的话像钉子一样扎在他耳边。他没回答,只点了点头。母亲偷偷在帆布袋里塞了点...
《碎光记忆 全集》精彩片段
《碎光》第一章:站在出发的车站1995年9月28日,沈砚十八岁。
那天阳光很好,镇上的风像是被水洗过,干净、通透。
他站在小镇火车站的候车厅里,脚边是一只蓝色的帆布袋,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一本发黄的诗集和一双未拆封的新袜子。
候车厅的广播喇叭像几十年没修过似的,发出沙哑的金属声。
候车室的木长椅被坐出了一层层油亮的光,角落里有个小孩在哭,母亲没说话,只是不停地拍着他的后背。
沈砚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双手紧紧握着票根。
去省城的火车下午两点四十到站。
他在等,等这辆把他送出镇子的车,仿佛命运也被塞进了那节车厢。
“到了那边,先去找你二叔。
他在建筑公司,能帮你安排个工地干活。”
父亲的话像钉子一样扎在他耳边。
他没回答,只点了点头。
母亲偷偷在帆布袋里塞了点腊肉,还藏了两百块钱在夹层里。
她叮嘱他别吃太快,也别随便借人钱。
他当时笑了笑,说:“知道了。”
但没告诉她,他其实最想带走的是墙角那本《新诗鉴赏》。
那书是他从镇中学图书馆“借”出来的,一直没还。
沈砚不愿当泥瓦匠,他想写诗。
但他知道,这念头说出来就是笑话。
沈砚出生在这个小镇北边的旧工人宿舍里。
小时候家里穷,吃一根香肠能高兴一整天。
父亲脾气暴躁,母亲沉默寡言。
他从小不爱说话,但喜欢写,五年级开始模仿海子写诗,初中写信给市报的副刊编辑,偶尔被刊登,稿费两块。
他把每次发表都抄在一本黑色作文本上,像是在积攒某种可以逃离现实的力量。
可这些都不能当饭吃。
他没考上大学,高考差了二十三分。
成绩公布那天,父亲没打他,只是在门口抽了一晚上的烟。
母亲炒了一盘西红柿炒蛋,一家人默默吃完。
“男的嘛,早晚要扛起家。”
父亲说。
扛起家,对沈砚来说,是丢掉诗的那一刻。
火车准时到站。
他站起来,肩带勒进骨头,但他没吭声。
那一刻,他是主动要离开的。
不是逃,是出发。
站台上灰蒙蒙一片,人群拥挤,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挥手。
他走在中间,没有人送他。
但就在他踏上车前几秒,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沈砚!”
他猛地回头,是苏婉。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连衣裙,鞋子有点旧,头发随风飘着,脸上有一点泛红。
她喘着气,小跑着靠近,把一个塑料袋塞进他手里:“给你……路上吃。”
“你怎么……”沈砚话没说完,喉咙就哑了。
“你走也不说一声。”
“我怕你会哭。”
苏婉笑了,眼里有光:“我不哭。”
她没哭,可他几乎要哭了。
他低头看袋子,里面是一瓶水,两块她亲手做的糯米团,还有一张折起来的小纸条。
她站在站台边,看着他上了车。
火车启动,她没追,只抬起一只手,轻轻挥了挥。
沈砚靠在窗边,看着她的身影渐渐模糊,像是水面上的倒影,一阵风就能吹散。
他没拆那张纸条。
他怕自己会后悔。
火车一路北上,车厢里人声嘈杂,蒸汽味混着饭盒的油腻味,让人头昏。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连绵不绝的山。
他想起小时候听父亲说过:“山那边没有啥特别的,就是别人的地儿。”
可现在,他想过去,哪怕摔下悬崖,也比在这镇上烂掉好。
到了省城的第二天,二叔带他去建筑工地。
工地在市区边缘,一大片黄土地,一排排临时板房。
他领了一身工作服,搬水泥、拉钢筋、挖沟渠,全是体力活。
“你年纪轻,别矫情。”
二叔拍着他肩膀。
沈砚没说什么。
他不怕脏不怕累,他怕的是——在这城市里,他什么都不是。
有一晚,他站在板房门口抽烟,头顶的灯泡晃晃悠悠。
他看着远处市区的灯火,忽然想哭。
他想写点东西。
可是他发现,手指裂口太多,写字的时候笔都握不稳。
他那本黑色作文本,就放在床下的箱子里,一直没再翻过。
时间像一根粗绳子,把人一寸一寸往后拖。
他二十岁生日那天,只在食堂加了两个菜。
吃饭时他突然想起苏婉,想起那张一直没拆的纸条。
夜里,他终于打开它。
“沈砚,如果哪天你累了,就回来看看我。
你写的诗我都记得,我相信你以后会是个作家。
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钢筋水泥的一部分,你有光。
——苏婉”他抱着膝盖坐在床上,整晚没睡。
第二天他去邮局给她写了封信,但没寄出去。
他怕她已经忘了。
他默默地把信烧掉,灰撒在工地角落的土里。
他
想,也许有一天,这些字会变成一朵草,没人注意地长出来。
几年后他换了几份工,去过汽修厂、快递站,还当过保安。
他学着不再写诗。
他的手变得粗糙,脸开始晒出斑点。
每次回老家,父亲总说:“你变得像个男人了。”
可沈砚知道,他只是越来越不像自己。
直到二十五岁那年,他遇见林婧。
林婧是个开朗的女人,在一家火锅店当收银员。
他们相识是在楼下的小超市,沈砚帮她提了袋米。
那之后,他们聊了一个月,搬进了同一个出租屋。
她说她喜欢安稳的男人,不会花言巧语的最好。
沈砚没说过“我爱你”,但每次她下班晚了,他都会给她泡好脚水。
他们结婚很快,没有婚礼,只在民政局门口吃了碗拉面。
婚后第二年她怀孕,沈砚喜极而泣。
那天他跑去工地领工资,又跑去婴儿用品店买了一堆婴儿衣服。
他说:“这孩子,一定会比我活得好。”
可他不知道,命运有时候会突然收回你以为握住的东西。
五个月后,孩子胎死腹中,林婧情绪崩溃。
他抱着她整晚没合眼。
医生说,是意外,责任没人能负。
自那天起,林婧开始夜里失眠,沈砚则开始梦见小时候自己在小镇的溪水边,一只纸船被风吹走,他拼命追,却怎么也抓不住。
那是他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他可能这辈子都抓不住什么了。
第二章:她是远方的河流沈砚第一次见到苏婉,是在初中二年级的数学补习班。
那天她穿一件白底碎花衬衫,坐在教室最中间的位置,低头写题,手指纤细,像极了他诗里描写过的“会说话的柳条”。
补习老师姓陶,是个性格急躁的中年男人,经常把粉笔头砸向那些做错题的学生头上。
苏婉却从没挨过一次骂。
她成绩很好,是全镇重点培养的“市中预备生”。
据说她家开布店,在镇上还算殷实,但她从不张扬,作业本整齐、字迹娟秀,每次考试后都会在纸角写上一句诗句。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沈砚就是因为这句话,才第一次鼓起勇气跟她说话。
他借了一支笔,其实他明明带了两支。
“你也喜欢写诗吗?”
她问他。
他有些紧张,耳根发烫,点头:“嗯,喜欢海子。”
“我也喜欢
。”
她轻笑了一下,“我最喜欢他写的那句——‘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沈砚愣了愣,心里像被一阵风吹开。
从那以后,他们偶尔会一起走回家。
她住镇东,他住镇西,半路要分开。
每次分岔口他都想多站一会儿,但又怕她看出什么。
她会笑着说“明天见”,然后像只轻盈的猫,转身跳上窄窄的巷口台阶,消失在昏黄的灯光里。
沈砚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喜欢上她的。
也许是某天她给他折了一只纸鹤,也许是她在下雨天递来一包干纸巾;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她一出现,世界就亮了一点。
他开始偷偷写关于她的诗:她是河流倒映我渴望的天空我不能靠近也不能离开可这些诗他没给她看过。
他怕打破那种“只是朋友”的安稳。
他知道自己和她不是一路人。
她要去市中,他可能连镇高都上不了。
他的未来是一片水泥地,而她,是流动的光。
高三那年冬天,小镇下了一场多年未有的大雪。
校园白得刺眼,广播里放着《一剪梅》。
全镇都弥漫着一种即将告别的气息。
那天他约她出来,说是帮她补习。
其实他想送她一样东西——他写的一本手抄诗集,封面用牛皮纸缝成的,里面全是他写的关于她的诗。
他们坐在镇图书馆后面的石凳上。
雪落在她肩上,像静静燃烧的火花。
他迟疑了一下,把那本诗集递给她:“这个……送你。”
她翻开看了几页,笑着说:“你写的?”
他点头,心跳得像鼓点:“你……喜欢吗?”
她没直接回答,只轻声念出其中一段:“你走在雪地里,不回头,但我知道,每一片落雪,都有你的影子。”
她合上诗集,眼角像是闪了一点湿意。
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说:“你写得很好……以后,不要放弃写。”
他没问她喜不喜欢他。
他知道,那时候问出来,就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高考后,他落榜,她考上了市中重点,被推荐去省重点大学的预科班。
镇上贴出榜单那天,他站在人群后,看着苏婉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有人在喊:“苏婉真是我们镇的骄傲!”
也有人在说:“那谁,沈砚,好像落榜了吧?”
他低头走开,没回头。
几天后,他收到她的一封信。
字很工整:“沈砚,我知道
你难过。
我不是劝你别难过,而是想告诉你——你有你的路。
考试不能决定你是什么人,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一个。
我会一直记得你写的诗,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在书店看到你出版的作品。
加油。
——苏婉”他把那封信藏进了课本夹层,一直没有回复。
他不敢。
他怕自己一旦写了回信,就会沉溺在那个永远无法靠近的她的幻象里。
1996年春,他听说苏婉已经离开镇子去了省城。
他站在曾经分叉路口的小巷口,望着那段她走过无数次的台阶,忽然觉得整个镇子都空了。
那年,他开始打工、写工地日志、偶尔偷偷写诗。
他写的最多的,还是她。
他甚至幻想过重逢。
幻想自己某一天成名了,她会在人群里看见他的名字,笑着说:“我就知道,你能做到。”
可现实不是小说。
他只是个工地搬砖的小工,每月工资刚够生活。
而她,可能已经坐在大学课堂里,听着高级文学赏析,和同学讨论博尔赫斯、加缪、佩索亚。
直到1999年,他收到家里来信,说苏婉订婚了。
对象是镇上派出所副所长的儿子,家境不错,人在市里。
婚期定在国庆节。
他在工地上看完那封信,站了很久。
那天下了暴雨,他却没有回板房,任雨水打在身上。
他感觉自己在某个不知名的节点上彻底失去了什么。
后来他试图不再想她,把她写进诗里,然后撕掉;烧掉;埋进工地废墟里。
可她像河流,越想忘,越流得深远。
2003年,他们真的重逢了。
<那天他在市图书馆办借书证,正要离开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沈砚?”
他猛然回头,苏婉站在那儿,穿着一件米白色风衣,头发剪短了,气质依旧温婉,脸上多了几分沉静。
他愣住,声音卡在喉咙里。
“真的是你。”
她走近了一步,笑得像当年一样清澈,“我还以为认错人了。”
他们坐在图书馆旁边的咖啡馆里,聊了很久。
他知道她已经离婚,一个女儿判给前夫,现在在市里一家出版社做编辑。
他没问细节,也没说太多自己的事。
只是听她讲,她当年怎么一个人撑过婚姻的裂缝,怎么独自去考编辑证,怎么坚持每个月看两本诗集。
“你还写诗吗?”
她问。
他苦笑着摇头:“不写了。”
“为什么?”
“没什么好写的。”
她没说话,只是轻轻放下杯子,说:“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出版第一本诗集。”
他心头一震,像是压了很多年的闸口被打开。
他低声说:“我以为你早忘了。”
她轻笑:“你是我青春里唯一的浪漫,我怎么会忘。”
那晚他们告别时,她说:“我们是不是老了?”
他看着她眼角浅浅的细纹,却觉得,她和当年一样,只是流得更深,更远。
“老了,”他说,“但河还在流。”
第三章:水面下的生活沈砚和林婧结婚那年,是2005年。
他们租住在市郊一处老旧小区的五楼,没有电梯,楼梯拐角总有刺鼻的霉味。
房子小,墙皮脱落,冬天冷得像铁屋。
可沈砚觉得,那是他人生中最像“家”的地方。
至少,有光,有人等他回去。
林婧很安静,做事利落,说话从不拐弯。
她没读多少书,但心细,有一份稳定的收银工作。
她说话时不喜欢直视对方,眼神总有点飘忽,但一笑就特别好看,嘴角弯弯,像个不小心打开的信封。
她怀孕后,情绪变得敏感。
有一次只因沈砚晚回家半小时,就在厨房哭了。
他抱着她,手足无措,只能一遍遍地说“对不起”。
“我不是怪你。”
她说,“我只是太怕了。”
“怕什么?”
“怕你走了,不回来。”
沈砚怔了一下。
他从没想过在别人的世界里,自己是重要的。
他握紧她的手,说:“我不会走。
我从没真的属于过哪里,这里,是我第一次想留下来的地方。”
她靠在他怀里,小声说:“我信你。”
孩子出生前,他们给他取了名字,叫“沈澈”。
林婧说,“要像清水一样,干净、透明,不像我们,都是混沌里长出来的。”
沈砚点头,心里像长出了新芽。
他开始接更多的活,凌晨四点去批发市场卸货,白天再跑工地,晚上回来还要洗衣做饭。
他的背越来越弯,手掌起了老茧,但他从未抱怨。
那是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被需要”的幸福。
他甚至又偷偷写起了诗,只是再也不是为了苏婉,而是为肚子里的那个小生命,为林婧,为那个五楼狭小却温暖的家。
“你是我写过最真实的句子每一笔都是生活给的墨。”
可命
运总喜欢在你低头种花的时候,狠狠一脚踩碎你的泥土。
孩子胎死腹中,医生的说法是“脐带扭转”,没人能预料,也没人该负责。
林婧失声痛哭,脸贴在医院冰冷的墙上,像是把所有力气都哭了出来。
那晚,他陪她在医院待了一宿。
她像块碎掉的陶瓷,一碰就裂。
他用手轻轻拍着她的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回到家后,林婧开始变得沉默。
她晚上常常盯着天花板到天亮,白天也不怎么吃饭。
有几次,她站在阳台上发呆太久,他一推门,她却说:“我只是想看看楼下的人。”
沈砚开始害怕。
他怕她走,怕她恨自己没能保护他们的孩子。
他不断迁就她,给她买她以前爱吃的小零食,半夜跑出门只为买她想喝的那款牛奶。
可她都没碰。
有天夜里,他听到她在卧室里念一句话,反反复复地念:“他是不是来错了时间。”
沈砚走进去,轻轻抱住她。
她身体僵硬,但没有挣开。
“不是来错时间。”
他说,“他只是短暂路过,留给我们记忆。”
她忽然崩溃,像崩塌的大坝,用拳头打他,用尖叫撕裂这个空间。
那一晚,是他们婚后第一次真正吵架。
也是第一次,他感到某种不可控的力量在家庭内部发酵,像慢慢膨胀的黑洞,把两个人往不同方向拉扯。
林婧开始频繁失眠。
她辞了工作,每天窝在家里不说话,有时候一整天不开灯。
沈砚不敢逼她,只是努力维持日常。
可他白天的工作越拉越长,回到家时,只能看见她坐在沙发角落,像一尊静止的雕像。
有一次,他想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她却大声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
“不,我只是——你就是这么想的。”
“不是,我只是担心你。”
“你根本不懂我。”
他无话可说。
他是真的不懂。
他不知道一个女人失去孩子后,是不是会永远失去某部分灵魂。
他也不知道,爱一个人,除了尽力陪她痛,还能不能做更多。
某天凌晨,他在楼下偶遇邻居老吴,抽烟时老吴说:“我听说你媳妇这段时间状态不好,你得小心点。”
“她不会做傻事。”
沈砚说。
老吴摇头:“我不是说她……是你。
她现在看你,眼神都不一样了。”
沈砚心里一沉。
那天回家,他试着跟林
婧谈心:“我们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散散心?
换个环境也许……”她忽然笑了:“你是不是受不了了?
你想逃?”
“我没有,我只是觉得——你就说你后悔了。”
“我从没后悔娶你。”
她盯着他看了很久,像是要把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解剖出来。
那晚她没再说话,只是默默躺在床上,背对着他。
他坐了一整夜,直到天亮。
2006年,林婧提出离婚。
她说她累了,也不再信未来。
她说:“你是个好人,但我不想再拖你下去了。”
沈砚没有挽留。
他知道,太多裂缝无法缝合。
他签了字,搬出了那个五楼的家,连那本诗集都没带走。
离婚后,他换了城市,做了夜班司机。
晚上接送喝醉的人,白天窝在出租屋里睡觉。
他不再写诗,不再提过去。
他告诉自己:“一切都过去了。”
可有时候梦里,他还是会看见那个孩子,穿着雪白的小衣服,站在阳台上,笑着对他说:“爸爸。”
他总是惊醒,额头全是冷汗。
三年后,他再次听到林婧的消息。
她自杀了。
是在一个清晨,跳楼,没有留下遗书。
消息是邻居老吴发来的:“我知道你们已经不联系了,但她的事,你有权知道。”
沈砚整整坐了一天,什么都没做。
那天晚上,他又梦见了林婧——她穿着当年结婚时那件旧蓝裙,坐在厨房的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他跪下来,抱住她的腿:“对不起,我没能救你。”
她轻轻说:“不是你的错。
只是我太累了。”
梦醒后,他第一次在很多年里写下一首诗,短短几行:你是水面下的河流无声却将我整个淹没第四章:牢笼之上沈砚真正明白“命运”这个词,是在他坐牢的第三个月。
不是进牢的那一刻,也不是宣判时,而是第三个月,一个清晨,他用冷水洗脸时看见镜中自己的脸,像一块被碾压过的石头,坚硬而模糊,所有的棱角和光芒都不见了。
事情发生得很快。
那天是2009年初秋,他照常开夜班车。
凌晨两点,一个醉酒男子坐进后排,一身酒气,还夹杂着血腥味。
沈砚有点警觉,但没多说。
车开到半路,男子忽然让他停下,说要抽烟,语气很冲。
沈砚本能地劝了两句:“哥,车上不能抽烟,要不忍忍
?”
谁知那人当场翻脸:“你谁啊?
开个破车还管爷?”
两人起了争执,那人摔车门下车,猛砸了车尾灯。
沈砚下车理论,对方突然挥拳打他。
沈砚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动手的,只记得那一瞬间怒火压倒了恐惧。
他拿起路边一个砖头……等他清醒过来时,对方已经倒在地上,头破血流。
他被当场拘捕。
那人是本市一家私企的老板,家里背景复杂。
事后虽然没有致死,但颅骨骨裂,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沈砚没找律师,只请了个法律援助。
判决下来的时候,他站在法庭上,没有辩解一句话。
“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他点头,仿佛是别人被判,不是他。
刚入狱那几天,他几乎不说话。
吃饭、睡觉、放风,每天像程序一样重复。
他跟其他人不一样,不抽烟,不聊天,不参与赌纸牌。
他只是一直写——不是写诗,是把自己这三十多年写成日记。
管教开始还以为他在装疯,后来翻看他写的东西,也没觉得异常,只说了一句:“像你这种没背景的,挺沉得住气。”
他笑了笑,没回答。
狱友里有个叫杜磊的人,五十来岁,犯的是诈骗罪,骗了自己亲戚两百多万。
他挺喜欢和沈砚聊天,没事就倚在床上说过去的事。
“我年轻时开面馆,谁来吃我都笑着。
后来不是碰了钱嘛,就飘了。
做生意哪有不贪心的?
可惜,棋走错一步,全盘皆输。”
沈砚问:“你后悔吗?”
杜磊咧嘴:“有什么好后悔的?
就是有点想我女儿。
她今年大三了,听说学得不错。
只是不知道以后还认不认我这个爸。”
沈砚点头,忽然有点羡慕。
他连个“还在某处活着”的孩子都没有。
杜磊说:“你呢?
你犯事,是不是太冲动?”
沈砚沉默了一会儿:“我那天没想那么多,只是突然觉得——这个世界,从来没打算对我讲理。”
杜磊没再说什么,只拍了拍他的肩。
监狱有个图书室,藏书不多,沈砚几乎读完了所有能读的。
他重读了《边城》、《黄金时代》,还有一些早年的诗集。
白天他装作在劳动,晚上回到床铺就写。
他不是写诗,是写一本小说。
他给它取名《碎光》。
他写自己的童年,写苏婉,写林婧,写那个从五楼走下的自己,
写那个拿着砖头砸下去的瞬间。
他用几百页稿纸,写尽一个普通男人从希望到坠落,从爱到失去的全部过程。
他想过写给谁看。
但更多时候,他只是想留下点什么。
哪怕没人读,也想让自己曾经的那些痛不那么白白经历。
有次放风,杜磊看他发呆,说:“我看得出来,你以前一定很有才。”
“才?”
他笑,“没有,活下去的才。”
杜磊说:“你知道你像什么吗?
像个已经烧完的火柴头。
外面黑了,里面还在冒光。”
沈砚低头笑了一下:“你说得挺诗意的。”
杜磊拍了拍他:“你出去之后,好好活。
不要像我一样,一错再错。”
他点点头,没说话。
出狱那天是个阴天。
门口没有人接他。
他背着狱中发的帆布包,走出高墙大门,才发现自己连去哪都没想好。
城市没变,但像跟他没了关系。
他像一个被遗忘的人,从一段剧情中临时退场,回来时发现早就换了布景。
他没去找苏婉。
她几年前就移居南方,嫁了个外籍教师,生活平稳。
他也没联系老吴,老邻居早搬了。
他在车站附近租了个十平米的小屋,找了份夜班守库的工作,晚上给仓库登记进出,白天补觉。
有时候他想,也许他再也不会有朋友、家人、爱情,但他还能有字。
他用发黄的纸继续写《碎光》。
写他在牢里梦见林婧来找他,说:“你还在这里活着,说明不是我们都失败了。”
写苏婉在诗歌课堂上提起他的名字:“他是我见过最纯粹的写作者。”
写他自己,站在深夜街头,看着万家灯火亮起,想:也许我也曾属于其中某一个光点。
他终于在2020年冬天,把《碎光》写完。
全手写,一本厚厚的稿纸,封面上写了一句:“我不是为了被记住而写,而是为了不彻底消失。”
他把稿子寄给了一家小型出版社。
那是他曾经想过无数次的未来,但也是他不再执着的梦。
他想,不出就不出吧,至少我写过。
几个月后,他收到了回信。
“先生:我们认真阅读了您的手稿,《碎光》文字质朴,情感真实,有极强的生命张力。
我们诚挚希望与您出版合作。
请联系编辑……”他坐在邮局门口,看完这封信,整整发呆了一个小时。
他想起苏婉曾说:“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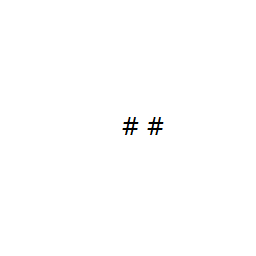
最新评论